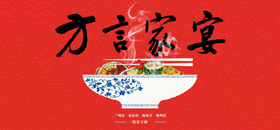《潮人家小国大 番批纸短情长》系列专题之一:辗转千里一番批,海邦剩馥百载情
《潮人家小国大 番批纸短情长》系列专题之一
《辗转千里一番批,海邦剩馥百载情》
作者:黄彩琼 卢仰 江永宏
“一溪目汁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火船驶过七洋洲,回头不见俺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时能回还。”
“无钱无米无奈何,背个包裹过暹罗。”
“钱银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
一首首凄惨的潮汕“过番歌”,唱出了当年潮汕人闯南洋“过番”谋生的艰辛,也唱出了“番畔钱银唐山福”供养潮汕百万民众的景况。
清代末年的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地,地少人多,大约占国土面积千分之一的区域要养活占全国百分之一的人口,贫困和饥饿如同梦魇般缠绕着每一个潮汕人。近忧迫使远行,潮汕滨海临江,战乱、灾害、贫困和绝望将很多潮汕人推向海外。鸦片战争后,千百万潮汕农民迫于生计,成年男子纷纷选择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开始当“番客”的苦斗之路。目的地也多为南洋,即现在的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潮汕方言称这些海外异邦为“番畔”。
过番,不但意味着失去家乡土地的农耕收获,失去家族依附,风险极大,不管是去还是回,去回之间都是茫茫大海,生死未卜。而且,还背负着一个家庭的部分甚至全部的希望,要养育留在故国家园的父母家眷、惠及乡亲故旧,生存压力和责任都压在“番客”身上。潮汕人把旅居海外称作“过番”,华侨称作“番客”,他们回国探亲称作“回唐山”。“番客”在异国他乡赤手空拳开始谋生,出卖苦力,做小手工,经营生意等各种营生。“钱银剋苦赚”,虽艰难困苦,但一旦站稳脚跟,立即寄钱寄物递送回家乡供养家人。
由于当时东南亚等国家金融邮讯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海外华侨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异国他乡筚路蓝缕、艰苦拼搏,以血汗换取钱财,在无法回家的情况下,要捎回家乡的款项和平安信息,只能通过往来海内外信得过的乡亲族人托送或者专门的“水客”带送,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家书和汇款“银信合一”的家书,潮汕方言将这种“银信”称为“批”,“番畔”寄来的银信就称之为“番批”。随着番批业务量的增加,相应出现了民间组织的联营商号,在东南亚各国及潮汕一带设行带运,这些商号称为“批局”。潮汕各地华侨以汕头埠为主,在各县设立“批局”分局,专门为华侨服务,潮汕俗语“番畔钱银唐山福”说的就是批局专门代“过番”在海外的人把钱物带回家乡。哪里有侨胞哪里就有侨批局。番批这种寄托方式,就这样诞生在跨国环境之中,成为海外侨胞眷属的经济生命线。
番批兴起于19世纪上半叶,直至1979年番批业务归口中国银行管理才完成历史使命,番批历经150多年历史,形成了独特的传统。番批主要分布在广东潮汕、江门五邑、梅州及福建的厦门、漳州、泉州和福州等地。它承载着华侨华人在海外艰苦奋斗的悲欢离合,饱含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
在处处充满险境与危机的异国他乡,流传着“六留一死三回乡”的说法。初次闯南洋的潮汕人所寄的第一封番批就是“平安批”,其意义一来报平安,二来表示牢记自己肩负的责任,这第一声问候里通常附上一点钱银,代表着打工顺利、不忘接济家属。而故土亲人亦会寄出回信,侨批与“回批”连结在一起,构成一条完整的亲情链,两张薄纸,便是亲缘血脉的彼此承诺。闯南洋的潮汕人通常在海上要漂泊两三个月,除了海盗、风暴、瘟疫,还有种种难以预料的突发灾难,最终有机会寄“批一封,银二元”的人,往往仅剩十之三四,“平安”同样意味着番客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实践,特别是在动荡的中国近现代史,“平安”二字时常显得难得甚至奢侈。所以这平安批就不单单是一封批了。之后的寄批回批,就成为了亲情和经济的双重纽带。粗略统计,潮汕地区留存下来的番批约20万件。它们真实记录了中国海外移民艰辛奋斗的心路历程,也见证了中华儿女开拓进取又不忘根脉、身处异地仍心系家国的深厚情怀。
下南洋“过番”不同于国内人口大迁徙的“走西口”“闯关东”,“番客”是去在海那边的异国他乡,语言文字、礼仪风俗、制度法律全然不同。迫于生计,他们多为苦力,日夜劳作,如在荒山野岭、虎狼出没之地开垦种植,如在矿区、橡胶园干活,生存环境和劳动环境相当恶劣。然而,他们只要能够尽快赚到养家糊口的钱银寄回家乡,他们什么苦都愿意吃,恪尽赡养亲人的责任。一旦站稳脚跟,事业有成之后,更是乐善好施。
1931年后,有一半的潮汕家庭靠侨批生活,因此潮汕有“食侨批”“食番批”的说法。潮汕侨眷人数众多,祖籍潮汕的海外侨胞有1500多万人。比如普宁原流沙镇,海外侨胞有9.3万人,侨眷及港属达11.27万人,分别占全镇总人口的59%和71.5%;潮安庵埠镇,海外侨胞7万人,侨眷及港属近10万人,分别占全镇总人口的50%和70%。19世纪至20世纪初,仅汕头的水客就有800人之多,并成立“南洋水客联合会”。每年通过水客带回国内的批款数以千万元计。据统计,解放前的潮汕地区,靠“番客”寄回批款为生的民众,约占总人口的一半,有些乡村如揭阳伯劳村则占当地总人口的七八成;如以侨眷家庭为单位计算,平均每月所收到的批款,约占家庭总收入的八成。民国期间,当时每年汇入潮汕地区的批款约八九千万银元,金额最高的1930年达1亿元。1947年至1949年的3年间,潮汕共收到海外侨胞寄来的侨批500多万封,批款总额约3.2亿港元。这些批款,不但养育家人、辅助亲友,而且修桥筑路、兴学办医,极大地促进侨乡的发展,也弥补了潮汕长期外贸进出口的逆差。
据国学大师饶宗颐总纂的《潮州志·商业》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侨批局达541家。在侨批业兴盛时期,潮汕地区的侨汇有80%是以批款形式通过批局汇入。侨批具有金融服务功能,写明批款金额的侨批就是一份“信用凭证”,蕴含着忠义孝悌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而不同时期侨批业商号对侨户的重信践诺,是“信而有征”“无征不信”的生动诠释。一封封侨批,体现了可贵的重信守诺。侨批从侨居国递送到侨眷手中,辗转千里万里,靠的就是“诚信”二字。
矗立在汕头小公园开埠区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全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我们在汕头侨批文物馆参观,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记载了侨胞在异国他乡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进取、勤劳、开放、包容、奉献的华侨精神,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在海外的结晶。他们不忘传承爱国爱乡的中华文化,无论身处何地,都时刻心系家乡祖国的发展,同时也尽己所能在家乡投资兴业、报效桑梓。
我们看到一封惜墨如金的“番批”:“人在银二”批,“人在”,报的是平安,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包含着丰富的感情,有思念、有安慰、有坚韧。“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另一张侨批上,印尼华侨陈君瑞寄给母亲侨批信封上的“难”字醒目异常。右侧一个大大的“难”字占了纸面的2/3,左侧附诗一首:“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梓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一个“难”字,写尽侨胞出洋谋生的艰辛和对家乡的思恋,但他们却时刻不忘赡养家人的义务。难,不是颓废和困难,而是主人公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的内心独白;我们看到一封署名“陈莲音”的批信,这是一封少见的女性番客寄给母亲的信。信中说,她“在街边卖霜尚无从维持生活”,但听闻母亲受伤,“故而节省日常用费”给母亲寄钱,这份孝心令人感动;“吾侄教育费事当尽绵力,寄去毋须多挂也,吾侄年青,须要努力攻读以期有成,服务国家社会……”这一封番批,不多的文字流露着中国人最朴素的家国情怀。
番批里闪烁着很多令人动容的语句:有父亲为不曾谋面的孩子取名的,有儿子问候双亲的,有父亲要求赎回被卖女儿的,有父母鼓励儿子发奋读书的……
番批有相对集中的邮寄季节,收批的时间集中在清明、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前后。限于“番客”自身的文化水平,番批大多数由粗通文墨的“秀才先生”根据寄信人的口述代书写,按字收费,大多写得言简意赅。信中所述种种,有的是对海外打工情况的叙述,有的是对家中父母妻儿的思念,有的是对所寄钱银的分配,有的是对送信“水客”应与厚待的叮咛,无不体现寄信人“番客”对长辈的孝心和对故乡的深情,焕发着中华传统伦理文化的人性光辉。
不计其数的侨批,记载了早期华侨的奋斗史,亦广泛涉及侨居国和祖居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国际关系等领域,是人类的集体记忆遗产和历史文化遗产,被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誉为“海邦剩馥,侨史敦煌”。
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侨批也被视为华侨历史文化的“敦煌文书”。
2020年10月1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参观侨批文物馆时这样说:“‘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加强研究,教育引导人们不忘近代我国经历的屈辱史和老一辈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并推动全社会加强诚信建设。
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长久留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番批作为诚信的化身,它在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和代表的意义都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网友评论
评论展示
-
华语环球2196用户节目效果特别棒,期待下一期的节目!求安排!!!
-
华语环球2569用户节目效果特别棒,期待下一期的节目!求安排!!!节目效果特别棒,期待下一期的节目!求安排!!!节目效果特别棒,期待下一期的节目!求安排!!!